| 我采訪過(guò)很多設(shè)計(jì)師一個(gè)同樣的問(wèn)題:“你希望給居住者設(shè)計(jì)的是一個(gè)什么樣的家?” 在回答中“舒適”是一個(gè)最常被提及的詞。 我試著為“舒適”描繪一幅場(chǎng)景:當(dāng)人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就像回到抵御洪流的堡壘,對(duì)于世界的驚慌逐漸緩釋,落坐于那張舒適的扶手椅上,眼前熟悉的一切讓人心安,與黑夜和解,窩進(jìn)干凈清爽溫暖的被子里,身體仿佛消失,呼吸平緩睡眠深沉…… 或者是諸如此類令人身心獲得撫慰的場(chǎng)景。 很少有人能說(shuō)清楚“舒適”到底意味著什么,那追求“舒適”又是在追求什么?當(dāng)“舒適”變成一種習(xí)以為常,更豐富的體驗(yàn)感是什么?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家讓人產(chǎn)生依戀,這種依戀里是不是有比“舒適”更為復(fù)雜的東西?  
阿爾托自宅,1934-1935,側(cè)立面與室內(nèi)。 
帶著這個(gè)問(wèn)題我采訪了一個(gè)新朋友S,她跟先生在徽州有一處第二居所的別墅。逐漸退隱之后,孩子們?cè)谕庾x書,日常沒(méi)有工作安排,她跟先生便從北京前往徽州,這也是他們住在徽州的第三年了,除了夫妻二人,家里還養(yǎng)了一條體型健壯的狗。 我問(wèn)道:“住在北京家里的舒適和徽州的舒適有何區(qū)別?”她的回答讓我頗為驚訝,細(xì)膩而深刻。 S說(shuō),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北京的家是向內(nèi)的舒適,你的房子可以做的非常高科技,但即使有個(gè)院子,人的生活一年四季也會(huì)被限制在房子里,因?yàn)樽匀画h(huán)境不好。徽州剛好相反,所有的舒適是在外面的,人可以長(zhǎng)時(shí)間在戶外,你并不依賴于房子技術(shù)的先進(jìn),可以有很多美好的體驗(yàn),去山水間、去村莊里,感受自然和文化帶來(lái)的魅力。人不是房子的囚徒,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更好,身心就會(huì)更加愉悅。 最后她說(shuō)了句,生命最大的意義是離開房子,家,適度舒適就好,人要走向自然。  
S位于徽州的家附近風(fēng)景及家里的狗狗。 當(dāng)我們身處一個(gè)無(wú)限追求快樂(lè)的時(shí)代,也就意味著我們竭盡所能在排斥痛苦帶來(lái)的消極情緒和體驗(yàn)。我們追求更加舒適的生活,例如智能的電子設(shè)備、自動(dòng)加熱座椅、電動(dòng)窗簾、貼合身體曲線的記憶床墊……但是在心理學(xué)家托德·卡什丹來(lái)看,吊詭的是,我們精神壓力的增長(zhǎng)其實(shí)來(lái)源于對(duì)舒適的追求。就像是人如果生活在無(wú)菌環(huán)境中,也必將被細(xì)菌給擊潰。 我的這位朋友并沒(méi)有研究過(guò)心理學(xué),但是在幾年的鄉(xiāng)村居住中獲得了一個(gè)真知,人對(duì)于“舒適”的追求是自我實(shí)現(xiàn)中很小的一部分,而面臨自然環(huán)境的不確定、不穩(wěn)定和復(fù)雜性,是她拓展自我的重要方面。適度的舒適是當(dāng)代生活的基本保障,在舒適之外有更多值得思考的部分。  
攝影師前田有步(Alfo?Maeta)沉浸在與自然萬(wàn)物混成的生命時(shí)光中。 
另一位朋友Ann在16年前就跟先生搬去了北京郊區(qū)靠山的別墅,并且成為了他們的第一居所。我印象很深11年前去她家地鐵需要一個(gè)小時(shí),再坐出租車半個(gè)多小時(shí)才能抵達(dá)小區(qū)。 居住在村里,從剛開始的不便,自己種植蔬菜,到慢慢發(fā)展出了新的技能,在后山森林里尋找生活的樂(lè)趣,到現(xiàn)在隨著房子的老化,一點(diǎn)點(diǎn)改變翻修。 我問(wèn)道:“不舒適的部分是不是也發(fā)展出了新的技能和心理耐受力?”Ann說(shuō):“是的,不舒適的確能提升人的敏感度和創(chuàng)造力,改變才是常住常新的基礎(chǔ)。住了16年還是很喜歡這里。” 我繼續(xù)問(wèn)道:“你說(shuō)的改變指的是什么?” Ann說(shuō):“審美的提升,關(guān)注身心的感受,不時(shí)的對(duì)身邊的環(huán)境、器物有所調(diào)整。”  
日本“隱士畫家”熊谷守一的日常生活,就是與螞蟻、青蛙、蜜蜂、蒼蠅……日日為伴。 在Ann的這番回答里,我看到了她對(duì)于“舒適”嶄新的理解,基本的生理舒適和相對(duì)復(fù)雜的心理舒適之間有著復(fù)雜的聯(lián)系。身體是溝通內(nèi)在與外在的通道,它幫助我們探測(cè)世界的舒適程度,并做出回應(yīng)。 對(duì)于居住舒適和便利的追求,成為現(xiàn)代人一項(xiàng)重要的生活目標(biāo)。人們對(duì)于“舒適”的理解變成了——一切“我”喜歡的事物,純粹,沒(méi)有模棱兩可、沒(méi)有陌生感。居住環(huán)境也應(yīng)該是取悅于人的,它帶來(lái)的是視覺(jué)的享受,是觸覺(jué)、嗅覺(jué)等感官系統(tǒng)的滿足。 我們傾向于通過(guò)外在物品來(lái)解決內(nèi)心的不安或者身體的不適,但是這種依賴越強(qiáng),在心理層面對(duì)于磨難的抵抗力也就越低。 似乎在生活條件越來(lái)越好的當(dāng)下,我們本該舒適、健康和快樂(lè)的生活,但是一切卻并不舒適。我們的心理舒適區(qū)不斷被壓縮,在心理學(xué)上有個(gè)詞“舒適悖論”,即盡管我們的生活中令人舒適的條件觸手可得,但我們卻對(duì)不適因素變得過(guò)度敏感。 在居住中所面臨的情況也一樣,盡管一切更輕松了,我們卻不敢稱之為更幸福。   
柯布西耶的海濱小屋,Le?Cabanon,1952 這是柯布自己的度假屋,也是他對(duì)于最小居住空間的一次實(shí)驗(yàn)。 
一旦我們將“舒適”作為一個(gè)概念,自以為掌握了其內(nèi)核,反而失去了創(chuàng)造性和復(fù)雜性帶來(lái)的吸引力。不如將對(duì)于優(yōu)質(zhì)居所的描述,變化為更具多樣、細(xì)膩和復(fù)雜的內(nèi)容。 阿蘭·德波頓在《幸福的建筑》中對(duì)家居空間的解讀,或許可以拓展我們的認(rèn)知。 在他看來(lái),家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情緒并不需要如何特別地甜蜜,這些空間既能向我們講述溫柔,也同樣能欣然地講述陰郁。家應(yīng)該成為一個(gè)能使我們更加牢靠地親近真實(shí)世界的地方,它包含被我們所忽略的,甚至是猶豫不決無(wú)力把握的部分。   
阿道夫·路斯,莫勒住宅,1927,奧地利 音樂(lè)室,從音樂(lè)室望向餐廳 從古羅馬時(shí)期維特魯威的“堅(jiān)固、實(shí)用、美觀”,到1927年格羅皮烏斯發(fā)展的“實(shí)用、耐用、經(jīng)濟(jì)且美觀”,再到1975年地理學(xué)家杰伊·艾普爾頓提出的“瞭望—庇護(hù)理論”。 環(huán)境對(duì)人的庇護(hù)性一再被強(qiáng)調(diào),但是以“庇護(hù)性”來(lái)回應(yīng)當(dāng)代住宅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不夠了,現(xiàn)代認(rèn)知神經(jīng)學(xué)研究認(rèn)為,人類的感官可多達(dá)33種。環(huán)境越是復(fù)雜,人們受到的感官和神經(jīng)刺激越是明顯。 我發(fā)現(xiàn),在跟大家談起幸福生活的模樣時(shí),極少有人會(huì)去描述那些讓身體舒適的器物,某個(gè)沙發(fā)或者某個(gè)電器,大家更傾向于描繪那些體會(huì)到幸福情緒的瞬間。 Li在廚房里最愉快的時(shí)刻,是從自家院子里采摘新鮮的蔬菜,她還種植了一棵檸檬樹和無(wú)花果樹。8月無(wú)花果熟透,她喜歡配上西班牙火腿、芝士,做一份鮮香清甜的沙拉;待到檸檬成熟,每日泡上一壺紅茶,香氣四溢的檸檬讓大家一起坐在院子里愜意閑談。  
紀(jì)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大部分的拍攝聚焦在坂本龍一位于紐約曼哈頓的家中。 從對(duì)于物質(zhì)空間舒適的追求,到尋找內(nèi)心空間的存在,才是追求幸福居住的健康路徑。 真正的舒適,或許是在保障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獲得的完整的生命體驗(yàn):我們或許不再追求某種裝飾風(fēng)格的完美,地板上傾瀉的晨光稍縱即逝的樣子更加動(dòng)人;離開功能齊備的客廳,望著庭院及四合的夜色,我們的身體與精神重新建立起聯(lián)系,那種靜謐足以忽略精致的家具;有限的居住內(nèi)容不足以支撐豐富的人生,而與無(wú)限自然的互動(dòng)中,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消亡…… 
路易斯·巴拉甘自宅,1948,墨西哥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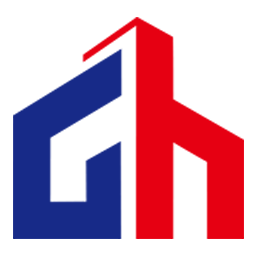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手機(jī):13720882598
手機(jī):13720882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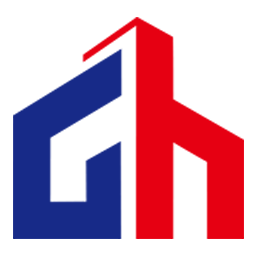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手機(jī):13720882598
手機(jī):13720882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