壘宏裝飾專業從事家裝,工裝,保證客戶花的每一分錢都物有所值,以下是壘宏裝飾的裝修心得分享:
江蘇連云港的一座高樓在大霧中若隱若現。 就像過去四年的建筑設計行業一樣,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 圖片和文字無關。 (視覺中國/圖)
2023年,給排水設計師陳泰被迫過著“退休”生活。
6月份,公司直言不諱地告訴他,“項目無法償還,情況非常困難”。 他的老板給他安排了“兩天休息五天”的工作方式,即每周工作兩天休息五天,工資也會減半。 結果,在路橋景觀設計單位工作了九年的陳泰,收入連生活費都不夠。 他的積蓄只剩下六萬到七萬元了。
2019年前后一股寒潮開始席卷建筑設計行業,四年來持續降溫,吹向更多新老設計師。 2023年,這場寒潮依然嚴峻。 最新消息是,7月,上海遠東建筑設計院有限公司被傳停工停產。 隨后,該公司澄清稱,停工的只是施工圖部門。 同月,撫順建筑設計院有限公司也宣布,全體員工放三無薪假。 三月; 更離奇的消息是,重慶一家公司的97名建筑設計師因“降薪太厲害”而選擇辭職。 公司以工作交接問題反訴他們,建筑師在一審敗訴后提出上訴。
這些圈外的消息讓人們認識到廈門室內設計工資,與中國房地產行業幾十年沉浮相關的行業已經進入寒冬。
減薪、辭職、倒閉
七年前,陳太主動離開家鄉,來到廣州“打滾”。
他告別家鄉的“養老”機構,來到廣州的一家私立設計院。 該院共有人員約150人,陳太從事給排水設計工作。 在新東家的領導下,他的工作量大幅增加。 他一年處理20多個項目,收入也暴漲。 到2021年,他的月收入將接近1萬元,年終獎可達2萬至3萬元。
據官方統計,陳泰從事的是工程設計這個龐大的行業。 據《2021年全國工程勘察設計統計公報》顯示,全國企業數量達23875家,可分為采礦業、加工冶煉業、石油化工業、建筑業等。 市政管理等七類。 其中,建筑及市政類與房地產行業密切相關。 常見的住宅、園林綠化、燃氣管道等都屬于這一類。
上升期在2021年戛然而止。陳泰記得,2022年新年過后,他迎來了一輪10%-15%的降薪,當年沒有發任何獎金; 2023年5月,他迎來又一輪10%的降薪。
疫情期間進公司的一位女同事,收入減少更嚴重。 “她只能掙廣州最低工資,每月2300元。” 最終,陳泰選擇了辭職。 我離開公司的時候,公司已經把辦公樓一樓的辦公室租出去了,只和另一家公司合用了一半樓層。
一切似乎都變成了一場耐力的游戲:據深圳一家國有設計院總建筑師翟雷的觀察,變化從2019年開始。建筑設計公司的大部分業務逐漸進入低迷期,項目大幅萎縮,導致建筑設計公司要么訂單銳減,要么項目落地后也難以回款。完全的。 設計師們逐漸面臨減薪、停發獎金等困難,直至無法忍受,主動辭職或被解雇。
2021年11月,加入河南一家民營建筑設計公司不到半年,嚴禾被告知不接受她的降薪請求,公司打算解雇她。 嚴赫告別了設計院。 但至少她得到了公司承諾的工資。
相比之下,包杰連全薪都沒有拿到。 2022年7月,包杰從985大學建筑專業畢業后,加入了天津一家民營建筑設計公司,月薪約6000元。 “這幾年都沒有年終獎了。” 她回憶說,公司經常因為“收款困難”而拖欠工資。 忍耐了一年后,包杰主動辭職了。 她聲稱公司還欠她不到1萬元的工資。

在員工苦苦掙扎的同時,建筑設計單位的經營者也在絞盡腦汁地維持著局面。 李泉成2010年在上海創辦了一家公司,主要為酒店、商業綜合體的電梯等項目提供專項設計。 他回憶說,十幾年的時間里,他已經賺了數億美元。 但在上海疫情和行業寒冬的雙重擠壓下,他只能先支付部分工資,待項目收到貨款后再補足剩余部分。 目前,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員工離開。
事實上,公司并不是沒有錢。 未收回金額達70至8000萬元。 李干成覺得60%到70%的錢還是可以追回來的,“但是你得起訴,不起訴就不給你了。” 他已開始司法程序。
曾在廣東經營一家建筑設計公司的鄧宗周在2022年結束了自己的公司。他記得,2019年公司還有近千萬元的業務量,但疫情很快摧毀了最后的繁榮。 公司巔峰時期有26人,現在只剩下鄧宗洲和另一位合伙人了。
鄧宗周也陷入了掙扎。 他經常投標和跑項目,并與其他單位合作嘗試陌生的景觀設計、室內設計和工程咨詢,但效果一般; 他要求律師致函催債,但沒有效果; 一些開發商已經破產。 ,起訴是沒有用的。 “資產清算的時候,就不會考慮我們這邊了。” 目前,他還有100多萬元沒有追回。
20 世紀 90 年代:白銀時代
55歲的翟雷在2022年發現自己的工資又回到了2012年的水平。
這位從業33年的建筑師感嘆,現在“不參與競爭,終究會被卷入其中”。 他的一生都被“卷軸”了:20世紀90年代,他放棄了穩定的工作,南下淘金;20世紀90年代,他放棄了穩定的工作,南下淘金; 步入中年的他,經歷了“三年買車、五年買房”的黃金時期,也想加入火熱的房地產行業。 如今,他第二次回到設計院,正等待退休。
與接受采訪的許多資深建筑設計從業者類似,翟雷的職業生涯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坎坷周期。 當大齒輪轉動的時候,建筑設計行業的小齒輪也開始慢慢轉動。
1990年,土生土長的翟雷畢業于長沙某985大學建筑系。 那一年,他被分配到家鄉一家國有工業設計院,主要為工廠設計廠房。
那些日子安穩又舒服。 翟雷回憶說,這個設計院以前是由某部委和當時利潤很高的汽車廠雙重管理的,待遇也相當優厚。 工作三年,我的月工資從70元逐年增加到300元、500元。 “工人們的工資只有四十、五十元(當時的月薪)。”
該設計院還負責住房分配。 員工結婚后即可分配20平米以上的房子; 工作兩三年后,只要結婚,就能得到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
不僅福利優厚,而且在老雇主那里也沒有熬夜、加班等“壞習慣”。 翟雷記得,看門的老人每天下午六點就把門鎖上。 手繪的時代,沒有電腦,沒有微信。 22歲的翟雷離開職場后,工作沒有任何后顧之憂。
這些都是帶有濃厚時代印記的待遇特點。 翟雷表示,當時該行業以部委所屬國有設計院為主。 也有省市所屬的地方設計院,但總體數量并不多。 為此,需要找設計院來做項目,有時還得靠人脈。 翟雷評價說,那段時間“很刺激,但沒錢”。
翟雷工作第二年,湖南人鄧宗周考入長沙另一所大學電氣工程專業。 四年后,他進入長沙一家設計院,主要為工廠做強弱電設計。 在他的回憶中,長沙的工作與翟雷的工作有些相似:每天工作8小時,工作之余還有時間喝茶看報紙。 設計院的環境布局與政府機構相當接近。 沒有展位,但是有一個小辦公室,專門負責水、電、通風等的工程師被分成一個辦公室。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經濟建設浪潮涌動,房地產業開始走上時代舞臺。
“特區建設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需要大量設計單位為其進行設計。” ” 翟雷說道。 1993年,他跳槽到鄧宗周設計院珠海分院。 據他觀察,當時流行內地設計院在特區設立分支機構,以搶占民用建筑設計市場。
翟雷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與老東家整棟大樓的奢華相比,珠海分公司只是租用一個小區的私房來辦公。 然而,他每天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0點,睡在辦公室后面的大樓里。
兩點一線的生活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到珠海的第一年,他的月薪翻了一番,達到了1000元。 但他仍不滿足,“項目不好,主要是低端住宅。” 翟雷想要出名,希望拿下醫院、紀念館、博物館等重點項目。
然而,翟雷很快發現,與能讓設計師出名的建筑相比,更能更快賺錢的卻是高周轉的住宅項目。 后來民用住宅確實為這個行業的快速發展敲響了鞭子。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啟動房地產改革,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支持了一系列相應措施。 從此,中國的住房制度走上了商品化、市場化的道路。
廈門大學教授趙燕京表示,此次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 他曾撰文稱,1998年全國住宅開工面積大幅躍升,達到1.6億平方米,比上年猛增近6000萬平方米。 隨后,該數據連續幾年快速增長。
金鑰匙已經在設計師手中。
2000年代:黃金時代
2004年,鄧宗周加入深圳一家公司,開始了他的建筑設計黃金時代之旅。 他記得當時深圳是中國的設計之都。 “深圳設計的影響力輻射全國。 到時候東南、西北、西北的項目基本上都會找到深圳。”

一年后,鄧宗周決定自己當老板,開設設計工作室。 2007年,工作室轉型為公司,專注于地產設計。
房地產繁榮已經到來。 2003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正式明確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房地產業發展駛入快車道。 以2007年為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當年房地產開發投資超過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0.2%,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3.2% %。 據新華網報道,當年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10.5%,創下近兩年來房價漲幅新高。 在深圳,房價自2006年以來連續23個月同比上漲10%左右,在北京,房價連續20個月上漲8%以上。
李干成描述,當時住宅非常流行,開發商根本不關心設計。 “他們沒有任何要求。 他們只有房間和東西。” 建筑設計行業逐漸進入黃金時代。 據2007年行業年報顯示,全國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比上年分別增長26%和50%。
鄧宗周順應了這一潮流。 他記得當時項目太多,他基本沒有參與投標。 他覺得這是“浪費時間”,他只從事他已經最終確定意圖的項目。 此外,他還可以接受大型設計院的外包項目。 在公司業務最繁忙的時候,還招收了“學什么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作為制圖員,經過簡單培訓后很快就上崗了。
到2012年,公司已有員工26人,能獨立設計的年薪達25萬元,而鄧宗周等創始人年薪可達70萬元以上。

2014年7月在深圳,正在建設中的深圳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深圳第一高樓。 (南方都市報視覺中國/圖)
幾乎與鄧宗周同時,翟雷也來到深圳一家國有設計院工作。 他也對這段黃金時期印象深刻:常年努力工作。 單個項目的建筑面積往往達到20萬-30萬平方米。 相比之下,這個數字現在已經下降到4萬至5萬平方米。
很快,不僅是住宅設計,翟雷理想中的公共建筑項目也紛紛效仿,與前者平分天下。 2004年參與西南某省級重點高中設計; 2008年,他設計了西南地區一所985大??學的校園。
當翟雷在快速城市化時期苦苦尋找機會時,2007年左右,美國留學歸來的李泉城進入了一家美國建筑設計工作室的上海分公司——外國公司也來到中國尋求發展機會。一塊餡餅。 工作環境令人羨慕:公司只用蘋果電腦,有咖啡機。 當時國家非常尊重國外機構的設計工作。 設計費用很高,交貨時間也很充裕。 李謙城每周工作四天,月薪1000美元,補貼1萬美元。 他“每天都過得很幸福,到處旅游、玩耍”。
沒喝過洋墨水的翟雷就沒有這樣的好處。 來到深圳的第一年,翟雷的年薪為8萬至9萬元,這在當時的深圳算是“低水平”,但他也有自己的挖金方式:加入“投機者大軍” “對于設計師來說。
“柴更”是一個帶有濃厚粵語背景的詞,意思是做日常工作之外的雜務。 翟雷記得,設計項目很多,一些小項目聘請設計院的費用非常高,不劃算。 有些方會私下找設計師與其合作,“快速且經濟高效”地完成項目。 于是,“炒作炒作”迅速在業內盛行。 每天5點30分下班后,翟雷就開始“攪拌”。 “炒”沒有明確的結束時間,也沒有確切的收入數額。 翟雷本人一年收入3萬到4萬元,他也見過有人“炒”賺的錢比自己的年薪還要多。 但如果你運氣不好,項目失敗了,你就一分錢也拿不到。

2010 年代:黃銅時代
翟雷或許還記得2012年:那一年是他來到深圳的第九個年頭。 與九年前相比,他的工資增長了兩倍多,達到20萬多元。 那一年,他將自己駕駛多年的國產車換成了德國車。
也正是從那一年起,翟雷和鄧宗洲感覺到,曾經的藍海逐漸變成了紅海。
翟雷注意到,國有設計院逐漸失去主流地位,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設計公司。 高薪從國有設計院招攬了一大批中青年骨干。 其結果是,曾經可行的項目無法在同一時間內完成,設計質量也很差。
但私營設計公司的日子也不好過。 鄧宗周覺得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建筑設計公司逐漸形成規模,但他的公司卻沒能跟上,難以抵御挑戰。 他回憶,從2012年開始,公司業務量每年都以10%的速度減少。
與此同時,李千成的悠閑歲月也結束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建筑設計單位數量猛增,不少單位為了搶占市場,展開價格戰。 他的感覺是,由于惡性競爭,自2014年以來,設計報價每年都下降20%。 與此同時,一批高周轉的房地產開發商涌現,建筑設計公司發現此類項目更容易承接,但代價是規劃周期縮短至2-3周,難以承接。以保證設計質量。
最終,在產業鏈中,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建筑設計公司在紅海競爭中逐漸將王座讓給了甲方,而在快速發展時期被忽視的陋習也逐漸顯現出來。
在單位內部,很多設計師都感受到深深的“擠壓”。 陳欽若自2018年參加工作以來,曾在深圳3家民營設計院工作,對于加班他并不陌生。 工作的前兩年廈門室內設計工資,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到10點下班,最夸張的是他在公司忙了兩天,沒有回家。 他只能睡在折疊床上。
這些無休無止的任務有時有點荒謬。 一位曾經在天津工作過的建筑設計師記得,她曾經做過一個城市設計項目。 效果圖基于實際城市場景的航拍,然后將設計融入其中。 由于航拍時是冬天,領導覺得不夠熱鬧,讓她加一束綠樹。
李虔成也有深刻的體會。 他評價這批高周轉項目“粗制濫造”:“商業規劃、商業定位、商業策劃、招商都需要事前考慮,但項目根本不考慮這些,只考慮開業” ”。 他記得有些項目甚至只有一層樓高。 它們都是設計錯誤的,導致后來無法吸引投資,設計師不得不進行修改。
然而,由于工作量巨大,像陳欽若這樣的草根設計師,工作第一年只能掙13萬元,這還比不上鄧宗周2005年創業前的收入。
設計單元的弱點成為了設計師的痛點。 鄧宗周記得,2018年左右,一家食品公司進軍房地產,找他做設計。 他評價說,這家公司的老板不懂專業工作,但喜歡發表意見。 最后從施工到機電方案他們改了七八次。 事實上,根據陳欽若的經驗,一個設計方案修改七八次是常事。
翟雷親眼目睹,2015年后,一批被單位淘汰的設計師轉身去了因棚子貨幣化而死灰復燃的房地產公司,成為設計院老板。 過去一年,每年連院長幾次面都見不到的員工,現在到設計院都得由院長親自接待。 不僅如此,這群人還根據自己的專業設計經驗提出了更詳細的設計要求,“我會整天拉著你開會,干這干那”。
2019年后:鐵銹時代
對于行業何時會跌至冰點,不同的設計師有不同的判斷。 但對于翟雷來說,那一年無疑是2019年。他敏銳地發現,當年的項目太少了,他已經不能再“火”了。
他開始羨慕房地產公司的暴富。 最終,2019年,51歲的翟雷跳槽到了一家私營房地產公司。 不過,新公司目前還沒有項目。 在國有設計公司度過了大半生的翟雷自嘲自己在私營公司無法避免人事沖突,于是六個月后他又回到了原來的公司。
但他可能對此表示感謝。
在10余位受訪者中,上海某大型國有設計院項目負責人嚴海饒是2019年后少數獲得升職加薪的城市規劃設計師之一,年薪超過30萬元但即便如此,他也感覺很累。
在嚴海堯的記憶中,轉折發生在2020年。隨著政策和市場的變化,一批房地產企業很快就不堪重負。 “‘三條紅線’之后,我們所有的業主都將交給政府。”
嚴海堯開始外出尋找工作。 他必須為過去不關心的項目而奮斗; 有時甲方根本不想做這個項目,他必須說服潛在客戶參與進來,這是“非常卑微的”。 他甚至還虧本賺了一筆:一次競標,他的團隊獲得了第一名,但付出的努力并不等于收益,因為他們前期投入太多。 這一切只是為了出名,以便我將來可以從事其他項目。
陳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年來,有些當事人甚至要求“買大送小”,免費設計一個小工程。 為了維持與甲方的關系,單位不得不同意。
這些沒有產生實際產值的無用努力也可能是設計師感到“被壓榨”的原因之一。 嚴海饒認為這是某種惡性循環:設計師工資的50%可能是年終獎金,而獎金能否發放取決于項目資金能否償還。 一旦市場低迷,“如果項目臥底,我們以后就不會給你錢了,但實際上我們的設計早就完成了。” 越是這樣,領導就越會要求員工參與競標,拉攏甲方。
面對這樣的困境,陳欽若已經開始考慮轉行:“說是市場萎縮,但實際上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建筑設計。” 不過,他還沒有想好轉行后自己能做什么。
這也是很多設計師共同的困惑。 雖然事業處于上升期,但嚴海堯也在考慮轉行。 他的許多同事轉行成為產品經理,而其他人則進入交互設計和智慧城市項目。 他甚至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帖討論可能的職業轉變,但最近他已經停止發帖了。 他發現,那些看起來光鮮亮麗的行業,其實做起來并不容易。 更何況他現在已經29歲了,如果白手起家,競爭力會受到限制。 他計劃去一家大型央企從事城市規劃相關業務作為過渡。 兩三年后,他就會看看自己能往哪個方向發展。
2023年,翟雷在建筑設計行業已經經歷了盛衰周期。 他不想離開現在的雇主,也不打算轉行。 “各行各業都一樣,你看到盜賊吃肉,卻沒有看到盜賊被打。” 五年后,他將退休。 從此以后,無論這個行業有多么偉大,都與他無關了。
(文中所有姓名均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姜博文 南方周末實習生黃一楠
本站對作者上傳的所有內容將盡可能審核來源及出處,但對內容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其真實性及合法性。如您發現圖文視頻內容來源標注有誤或侵犯了您的權益請告知,本站將及時予以修改或刪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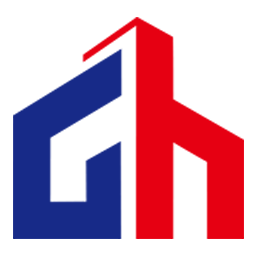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手機:13720882598
手機:13720882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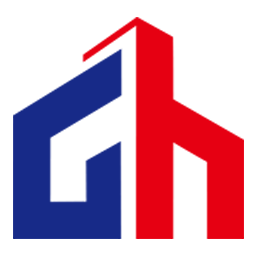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廈門壘宏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手機:13720882598
手機:13720882598